精读中篇小说旗煊二
那年春节,我们在广州的棠东村度过,这是一座离市中心较远、规模较小的城中村。为了节省金钱,我们住在一房一厅的出租屋里,她睡房、我睡厅。认识她的三年时间,我和她只做过一次爱,就是第一天在旅馆里那次。我记得离开旅馆之后我们坐上了客运车,开到半路,我尝试握住她的手,问道,我们现在算私奔的关系?她挣脱开,双手抱胸,说道,我们只是萍水相逢的朋友,开心同游,何必束缚彼此。我含蓄说道,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还不能确立恋爱关系吗?她陡然扯大嗓门:一起睡个觉就要谈恋爱吗,法律好像没这个规定吧,如果有,这个车都装不下我的男朋友们。整个大巴的人都听见了,纷纷侧目,当时我真想砸开车窗往外跳。从那句话到下车,我经历了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小时、60分钟、秒。甄心完全不在意,甚至偏过头去暗暗发笑。那次以后我曾几次碰她都被拒绝了,理由是,她当时问我是否爱她,我回答不能确定。男女同屋,却肉体分离,别提多煎熬了。我时常怀念她的裸体,脑海中深深印刻着她人鱼线上纹的那句鸟语,一直不敢问它的涵义。有时她只穿内衣在屋里走来走去,晃动的山峦带动地震,简直要我命。
我后来知道,甄心也不是她的真名,她每天换一个名字,说每天都是一次新生。她说,我老用一个名字实在无趣。我说,名字又不是我喊的,是你喊的,你有兴致可以每天叫我不同的名字。她悻悻地说,老娘才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呢。我说,苏天枢的天枢是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星辰千百年不变,我也一样。她噗嗤笑道,还好我没钱赌博,不然天枢兄跟在后面,还不天天都输精光。我说道,不用等赌输,现在我的口袋就是精光。她一拍桌子:干脆叫你身份证上的陈勇好了。我哼一声:我拒绝接受这个土得掉渣的名字!她笑道,有本事自己去弄个新证。我看过她的身份证,上面的名字是何芬,谁信啊。我明白,假身份证的名字一定要普通,这才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不会招来麻烦。那年除夕夜,我们决定不再啃干面包,要去吃一顿饱饱的麻辣烫,肉串不敢点太多,素串和粉条满满一筐。我舍不得多吃,心疼她那小身板。她呼哧呼哧大口进食,说今年的年夜饭是七年来最心满意足的一顿。我簌簌流下泪水,想家了。那天她的名字叫罗佩颜,这是早餐店玉米档口老板娘的名字。罗佩颜二世宣布完她的新名字,笑着说,她要沾沾老板娘的贵气,以后争取开家卖玉和卖米的店子。我有写日记的习惯,认识她之后,我的日记版头除了某月某日、星期几、天气之外还多了一项:她当天的名字。另外,我还坚持着写作投稿,因为经常搬家,很多稿费单都收不到,到手的部分不多,勉强能买点水果加点菜。
吃完年夜饭,我们去海心沙看小蛮腰(广州塔)。晚上风很大,我们牵着手、挺着大肚子在珠江边漫步。望着光线暧昧而梦幻的小蛮腰,我壮着胆,搂住罗佩颜的小蛮腰,再一次郑重提出恳求:做我女朋友吧。罗佩颜说,你我还是不合适。她并没有推开我,我依然搂着她,我们继续以让路人羡慕的姿势缓缓前行。我问道,这些年,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罗佩颜问道,你还有多少钱?我苦笑道,你当时不仅掰断了我的身份证,还掰断了银行卡,当时我的现金只有一千,现在剩下不到两百。罗佩颜倒还笑得出来,而且那个开怀:带着钱闯个鸟荡啊,闯荡就得挣钱养活自己,让你带一千出来算优待你了。我的脸耷拉成苦瓜:那请问女皇陛下,我们怎么个营生?罗佩颜说道,你先回去,明天大年初一,我们早上去广州酒家喝早茶。我一咋舌,广州酒家喝早茶那得好几百呢。罗佩颜自信满满道,老娘这些年混江湖可不是白混的,尽管回去等好消息吧。我问道,这么晚,你自己一个女孩子不怕?她捂住肚子笑弯腰:傻瓜,认识你之前我不都是一个人吗!
回到出租屋里,整晚我都没睡着,也联系不了她,只能空担心,导致我一夜无眠。天快亮的时候她回来,先去洗了个热水澡,带着潮湿的热气出来后,她从包里掏出一叠百元大钞啪一声拍在桌面上,笑道,数吧。当时的我别提多惊奇,后来才知道,那晚她用性感的小腿拦停了一辆保时捷。实在囊中羞涩她才出自下策,基本都是彻夜不归,偶然有几次带男人回出租屋,男人们都是衣着光鲜,不像出不起钱住酒店,倒像是猎奇尝鲜。日记里记载着她第一次带男人回来的情景,那天她叫布伦诗,男人穿着一件花衬衣,头发洋溢一股浓烈的啫喱水气味。进门后,布伦诗客气地对我和那个男人作了相互介绍,当时我真想撞墙,感觉自己成了拉皮条的,不对,应该是逼良为娼的恶棍。布伦诗把我拉到一边,问道,你要不要出去转转?我故作笑颜:一会还要帮你收钱呢。布伦诗笑道,也好,我最烦数钱。房间其实是没门的,只有一张帘子挡着,从前我在客厅是看着布伦诗的光洁小腿入睡,此刻多了一双毛茸茸的粗腿,恶心的感觉使胸腔的大海翻涌。我冲出屋子,九曲十八弯后,去到一箱啤酒跟前,身后是萦绕耳畔令人酥麻的叫床声。
脸颊被酒精彻底晕红之后,我开始穿行在城中村错综复杂的巷道,午夜漫游,黑暗中飞驰。汗水渐渐流干,速度慢慢慢下来,呼哧呼哧,一步一重天。墙壁上没有多一寸空白,统统贴着广告海报,同一个位置,前天贴迷药枪支假证、昨天贴招聘公关小姐,今天贴医治梅毒淋病,明天贴廉价招租放租,后天贴无痛人流药流……从前我觉得这种宣传是浪费时间的,认识布伦诗后,我开始相信有一种隐秘的人存在,数量庞大却悄无声息,因为无所禁忌,所以在残酷现实面前悠然自得。凌晨零点了,人潮依然汹涌,一眼望去黑压压一片,夜市的灯光把人们的脑袋打亮,无数的电灯泡在碰撞、发热。透过握手楼、亲嘴楼的狭隘缝隙望向天空,我发现,夜空原本漆黑一片,当缩小到一定程度,它会像夜明珠一样渗出微光。
极度劳累之下,人反而头脑清醒。我开始为自己爆发的情绪感到可笑,我跟布伦诗只是同行的旅伴,我也表明过不是真的爱她,干嘛不能宽容一点?她一个女孩子长期漂流在外容易吗?也许肉体是她最方便携带的营生工具吧。于是,我又返回到出租屋里。男人已经离去。布伦诗光着身子坐在沙发上抽烟,是那种女式的薄荷细烟。看到我回来她一点也不惊慌,淡淡向我招手:来,帮我穿上内衣。帮美女穿内衣是一件无比奇妙的事,尤其是男女之间只有纯洁友谊的情况下。我动作很轻,不敢触碰关键部位,手指偶尔沾到她弹滑微暖的玉肌,内心便是一道闪电。她的乳房不算大,但胸型很好看,尖尖翘翘的,像两托出水荷蕾。扣上扣子后,她自己就不够贴合的地方再调整了一下,雪山绽放出寒光。我问道,还有必要穿内衣吗?她说,彻底暴露是无趣的,女人穿内衣是为了让男人脱。我呵呵乐了:那我帮你穿是什么说法?她说,女人可以很轻易让男人脱内衣,但有兴致让男人帮她穿上的,堪称凤毛麟角,你可想而知,你自己的地位。我笑道,我明白了,帮女人穿内衣的男人只有一种,那就是奴仆。她噗嗤一笑,然后凝神道,你呀,真是一个大傻瓜。当时我听不懂她的话,以为她的意思是指,我当了奴仆还浑然不知,傻气透顶。她说,今天我懒得想名字了,大作家帮我想一个吧。我思忖半晌,道,叫苏檐吧,屋檐的檐。她娇嗔道,檐字我喜欢,但我不要姓苏,苏大作家占我便宜,哼!于是,她那天叫方檐。她说,布伦诗已经死了,忘掉她吧。
晚上,方檐带回来一个女人,说是赚了钱给我发的福利,她更把床腾给我,自己在沙发上翻看《新华字典》。开始我有点拘谨,慢慢鼓劲,继而发狠,我要让女人的尖叫声震裂玻璃。期间,我听见方檐的一串木屐声,慢慢悠悠,上了趟厕所。我一下子疲软下来,动作也缓慢乏力,那个女人的声音依然保持高分贝,无可否认,她确实很敬业。那次以后,我不再为女人的尖叫声感到骄傲。生生折腾两小时,屋里留下我和方檐。她说,第一次跟三十多岁的女人做吧?我点点头,吹出一个烟圈。方檐说,三十多岁正是女人丰腴的巅峰,没到太嫩,过了就老,我总在想象着自己十年后是什么样子,如果那时我厌倦了闯荡,我能干什么?既然历史无法质疑、未来无法预知,我还是保持沉默吧。楼下的烧烤店人声吵杂,除了杯瓶的碰撞声外,我还听到火的吱吱。我话锋一转:有个问题我早前就想问你,我们认识的第一晚你留我在旅馆过夜,有想过让我付钱吗?方檐笑道,你是指房费?我深吸一口烟,道,你知道我说哪个钱的。方檐闭上眼睛,说,没有。我问,为什么?她幽幽道,如果每个人都收钱,那我就彻底成了一只鸡,但我是人,是女人,我要找一张长期的饭票太简单了,但我喜欢自由自在,一个漂泊四海的女人,多少擦肩而过的男人,可能一辈子都不再重逢,喜欢的就留个纪念吧,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迈出一步,就能把百年缘分上升到千年,功德无量啊,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多一夜情,难道都是性欲惹的祸,不,归根结底八个字,不想错过不想遗憾……她很少一个人说这么长的话,我姑且相信这是心底话。
其实方檐挣钱的手段远不止一种,援交只在放松和犒劳自己时才选择。她能胜任除体力活外所有的短期工作,而且雇主们没一个不喜欢她的,常常打赏,因此她总能挣得比别人多,三分耕耘七分收获。她花钱不多,甚至很多必要的开销都能被她奇迹般地省去,所以大部分时间都不用工作。玩了半年我们决定离开广州,我发现我们其实没有游到广州的多少地方,她分别用艾妮、李诗彤、黄蓉、范冰冰的身份发表她的高尚言论:一个角落不落下,走马观花,那是游客的行径,老娘是行者,大地行者!
相处久了,我认识到她的脾气其实是比较冲的,爱恨分明,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缘故才慢慢能包容许多事,这也许是她当年毅然决然远走他乡的关键原因。记得有一次在宜昌,我们坐公交车,一个老男人趁拥挤抓了一把她的右乳,她二话不说,一个响亮耳光。摁倒老男人之后,一边骂着臭流氓一边拳打脚踢。我自然免不了要掺和几脚。顾忌到公交车上有视频监控,下车后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回家收拾走人,不到两小时,我们已经坐上去往襄阳的客运车。踏在襄阳的土地上,她觉得还不够解恨,又在旁边的电线杆上补踹了两脚,当时她穿着红色高跟鞋。这还不是我们遇过最恶心的事,有次在德令哈(我跟她说想看看诗人海子的德令哈),还是公交车,下车后我看到她衣服背后黏了一坨白色浓液,她骂道,妈的,哪个龟孙子往我身上吐唾沫!我用手指沾了点闻闻,是青草气息,立马呕吐一地,她拍着我的背问我怎么了。我咬牙切齿道,是精液!我相信,如果她当场逮到这个人,她一定会把他杀死。
第二年我和谢金玲去了北京,北京我只来过一次,是领一个小说的奖。谢金玲说她已经第五次来,要带我认识一个老朋友。这是个女人,我只知道她叫沙拉姐,三十多岁的年龄,漂亮、苗条、时尚,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其给人的感觉,那就是风情万种。我猜想,谢金玲之前对女人三十多岁年龄段的高度评价和向往是从沙拉姐身上感受到的。沙拉姐安排我们住二环内的五星级酒店,我和谢金玲住一间大床房,睡同一张床,但什么事也没发生。沙拉姐带我们俩整整玩了一个星期:八达岭长城、故宫、曹雪芹故居、鸟巢水立方等等。一周后的一天,谢金玲已经是张然。我们躺在床上。我问张然,沙拉姐是干什么的?张然嘿嘿笑道,啥事儿不用干,她老公身家上亿。我没有对沙拉姐刮目相看,反倒对张然刮目相看,我说,你赤手空拳打天下,居然也能认识这等上层人物。张然翘了翘嘴角,得意笑道,老娘的光荣史堪称辉煌,只是不轻易透露给你们这种凡夫俗子罢了,跟着老娘这座金矿山,耐心挖掘吧,有你好看的。看着这个长相娇媚可人的女孩自称老娘,我感觉又好笑又妥贴。我笑道,你也想钓个金龟婿吧?张然幽幽道,有钱人多是中老年,我不喜欢中老年人,只嫁年轻人。我问道,富二代?张然道,我不喜欢不劳而获的人,真要选,我会选勇于创业的有为青年,成功当然最好,如果失败那也是我的眼光出问题,我为自己的眼光负责,陪他一起经历失败。我笑道,没想到你还挺伟大。张然道,不过这还不是我最喜欢的类型,只算第三档次。我问道,那第二第一档呢?张然笑道,第二档是文艺青年。我呵呵笑道,是我这种吗?张然娇嗔道,切,你也算青年吗,年龄或许是,但心境太老,比大叔大妈都不如。我习惯了不去应对,正常人根本跟不上她的古怪另类思维。我继续问,那第一档呢?张然道,朋克青年,我喜欢那股疯劲儿。
当晚我们就去了一家摇滚酒吧,好的酒吧都是高消费,我和张然一般不去,这次是沙拉姐请的客。灯光又多又炫,五光十色,但怎么照,室内都是迷幻暧昧的黑暗。整片黑暗是由人们内心释放出来的一小片一小片阴郁和灰霾汇集凝聚起来的,因此无法照亮。酒吧不大,没有舞池,全场的焦点是中央的摇滚乐队,映入我脑海的只有两个模糊的影像:黑发像荒草一样飞舞,头颅像铁锤一样撞击。在嘈杂的环境里,我们说话是用吼的。沙拉姐问我们喝什么酒,张然说,威士忌热身,伏特加提神。沙拉姐会心一笑:臭丫头,鬼主意就是多。张然和沙拉姐心有灵犀一起说:优雅打头,壮烈赴死。我不得不佩服张然:光喝威士忌,肠胃不满意;直接伏特加,喉咙烧开花。那晚我们都喝得烂醉。我问,沙拉姐,什么时候带你老公来给我们认识一下?张然插嘴,我见过了,胖胖的,很敦实。沙拉姐突然抽泣起来,呜呜声中隐约听到一句话:敦实个屁,此刻都不知道在哪个女人的怀里呢。我说,有钱男人免不了沾花惹草,女人要想开一点,让自己活得开心。其实我只是安慰一下沙拉姐,没想到张然会一个大耳光过来,我原本被酒气熏热的左脸登时火辣辣的,像被泼了一杯刚烧开的水。张然义愤填膺地吼道,男人没个好东西,老婆这么漂亮还要出去鬼混,真该抓去剪了。我感觉下身一阵寒凉。张然续道,离婚吧,女人一个人也能活得很好。沙拉姐怯怯地说,但我还爱他。张然厉声道,但他已经不爱你了,一次不忠百次不容,就是你的容忍才让他如此放肆,离婚吧,分他一半身家,既惩罚他又保障自己下半辈子。沙拉姐道,我之前提过,但他硬是不离,他认识不少大律师,甚至认识法官,他一直拖着我也没办法。我试图挽回一点颜面:有他出轨的证据吗,如果有,申请离婚就很有利。沙拉姐道,一开始没注意这方面,撕破脸后他更小心了。张然一口干掉满杯伏特加,斩钉截铁道,我帮你!说完,她冲到摇滚乐队跟前,抢过主唱的麦克风,先是续唱完郑钧的《赤裸裸》,然后连唱三遍小红莓乐队的《zombie》,居然连原唱那种喉咙拉二胡的感觉都唱出来了,全场彻底沸腾。她回到座位后,酒吧老板还专门过来,称赞她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连续唱同一首歌三次不仅没被轰下台反而掌声雷动的歌手,问她愿不愿意在他的店里驻场演唱,说好几个当红歌星当年都在这里驻唱过,有机会一定给唱片公司推荐她。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酒店里写一首长诗。顾美鱼回来得很早,在床上放下包包后边走进浴室边脱衣服,洗了半个多小时才出来,嘴里发狠地骂了一句:妈的,油乎乎的,压死老娘了。顾美鱼掏出手机(沙拉姐给买的临时用品)丢给我,说,欣赏欣赏我拍的美照。里面全是顾美鱼和一个肥头大耳男人的裸照,镜头控制得恰到好处,顾美鱼三点不露,倒有那个男人的好几张正面全裸照,边上都有一条女人的长腿出镜。我一拍大腿:哈哈,这回沙拉姐的婚肯定能离成了,财产对半不成问题。顾美鱼详细讲述了整个经过:
按照沙拉姐的提示,顾美鱼下午去到沙拉姐老公胡飞腾的公司总部。公司是卖美容产品的,顾美鱼投诉一款瘦身茶的质量问题,说喝了之后整整拉稀三天三夜。顾美鱼在公司里大吵大闹,嚷着一定要见总经理,工作人员拗不过,只好请出胡飞腾。用顾美鱼的话说,她只用了三个动作便勾住了胡飞腾的魂儿。在那间狭小的谈话室里,顾美鱼先是捋长发,继而翘起二郎腿钓高跟鞋,最后前倾身躯起来,腰臀形成一张弯弓,把胡飞腾弹射到天上去。看到胡飞腾的目光死死盯住自己前倾时露出的乳沟,顾美鱼知道他已经坠落到她的峡谷。顾美鱼欲迎还拒,起身走人,淡淡地说对解释勉强满意。她走得干净利落,高跟鞋踢踢踏踏,把所有人的心跳都踩响。顾美鱼对男人很有把握,不出意料,顾美鱼还没走出写字楼大门,手机已经响起,她在资料里留了号码。胡飞腾在电话里说,希望代表公司请顾小姐吃顿晚饭,以表歉意。顾美鱼在电话这头已经笑得不行,但还是控制声音,保持淡然态度:既然贵公司诚意拳拳,那我们就去全北京最贵的那家吧。
后面的事就顺水推舟了,期间有个小插曲。他们入住酒店时正好遇到了胡飞腾的一个老相好,胡飞腾委婉提出想法,看能不能一龙双凤。顾美鱼啪地给了他一个耳光,骂道,混蛋,滚蛋!顾美鱼后来说,耳光是替沙拉姐打的,混蛋也是替沙拉姐骂的。当时胡飞腾掂量了一下,在老情人和新猎物之间选择了后者,低三下四、死皮赖脸地说好话,顾美鱼强压住心中怒火,露出一个僵硬的微笑。我问顾美鱼,你和他真做了?顾美鱼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我这是抛砖引玉,为了沙拉姐后半生的幸福和自由。我说,拍几张艳照就好啦,拍完趁机逃掉。顾美鱼说,这个贱男人警觉性很高,几次三番想拍照都不肯,我只能先把他搞累,怪不得这个死鬼会出轨,太他妈有活力。我道,你太伟大啦,简直就是神农以身试毒啊。顾美鱼不屑地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老娘阅男无数,多他一个算个鸟,以后我跟沙拉姐就真的情同姐妹了。顾美鱼突然两眼发亮,说道,我有一个想法啊,我经常会赚点男人的钱,其实那些男人基本都是背着老婆出来猎艳的,当他们老婆的女人多可怜啊,我要帮她们,拍好照片,跟踪那些男人,把照片发给他们的老婆。我哈哈笑道,婚姻杀手已经不足够形容你的可怕啦,你这是婚姻破坏神啊!
顾美鱼给胡飞腾发了个彩信,内容很简单,一张她和胡飞腾的合照,下面是沙拉姐的手机号码和一句话:我准备发给她。发送成功后立马关机睡觉,嘴角挂着笑意,她已经想象到胡飞腾那个热锅蚂蚁的样子。顾美鱼其实是个很容易满足的女孩子,那次我们去到上海的东方明珠,我们向保安咨询,门票太贵了,舍不得买,她悻悻地拉着我出来,大步流星绕着东方明珠走了一圈,走完对着车水马龙大声喊道,摩天大厦光高顶个屁用,占地也就巴掌大,老娘给它画地为牢装进去了。我问过她,这么一直在外漂泊,担不担心有天突然就死掉了?当时我们在一家小公寓里,她掀开衣角、拉下一点裤子,指着人鱼线上纹的那行字说道,你之前老是问我这行字的意思,知道这是什么语吗?我摇摇头。她得意笑道,这是古希腊语,荷马史诗《奥德赛》里的一句话:如果你听说他已死去,不在人世,那你就迅速返回亲爱的故乡土地,给他建造个坟茔。我笑道,看不出你还挺有文化,《奥德赛》都读过。她立刻背过脸去,冷冷地说,是一个男人带我去纹的。
第二天的顾美鱼叫林芙嘉。一清早就有人拍我们房间的门,我们赖在床上,谁都不愿意去开,轰轰轰,叮咚叮咚,拍门声与门铃声合成交响曲,不到黄河心不死。我只好去开门,打开一看,拍门的是一个圆脸壮汉,侧面站着沙拉姐。两分钟后我知道,这个男人就是胡飞腾。原来胡飞腾收到彩信后深知不妙,居然先下手为强,先向沙拉姐供出事实并求情。不用多想,沙拉姐能告诉他我们酒店的地址并跟他一起出现,他已经把沙拉姐拉回到自己那边的阵营。事后林芙嘉都后悔自己一时大意,竟然打草惊蛇,如果可以打个措手不及,就不会留机会给胡飞腾补救了。当时,胡飞腾扑通一下跪向床上的林芙嘉,林芙嘉冷笑道,你对不起的人又不是我,干嘛向我下跪?沙拉姐帮着口:他已经向我道过歉了,我已原谅他。林芙嘉道,那他干嘛还跪我?沙拉姐继续道,我们有孩子,我也爱他,不管有没有这些照片,我都不会跟他离婚,但我求你把照片还给他,他的公司正准备上市,这时候不能出负面新闻啊。说罢沙拉姐也跪下了。林芙嘉犹如火山爆发:我尊敬你喜欢你才叫你一声姐,我牺牲自己完全是为了帮你,你却反过来为这个混蛋求情,你让我太失望了,你不配当我姐!胡飞腾掏出一个油纸袋放在床上,说,这是十万块,你们先收下,不够的还可以说,我只求你把照片还给我,对不起。林芙嘉怒道,照片里还有我的裸照呢,凭什么给你!说完把手机重重砸到墙壁上,零件四散飞射。林芙嘉这等强劲气场,把我和他们俩都震得低下了头。林芙嘉对我厉声命令道,走,收拾东西!她自己穿着蕾丝吊带睡衣、赤着脚就蹬出了房间。当我提着行李下到酒店门口,林芙嘉正面向墙壁哭泣,看着那个婀娜迷人的背部一抽一搐,我心痛不已。我过去拍拍她,她立马挺直身体,擦干眼泪,不爽道,妈的,便宜了那个混蛋了,还三次。我掏出胡飞腾的油纸袋在空中晃动,道,不是白,有报酬的!林芙嘉又想一个耳光过来,这次我反应快躲开了。她狠狠地说,我不要这臭钱!
(未完待续)
本文刊于《都市》年第二期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hdnzm.com/wadzz/13041.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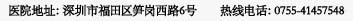
当前时间:
